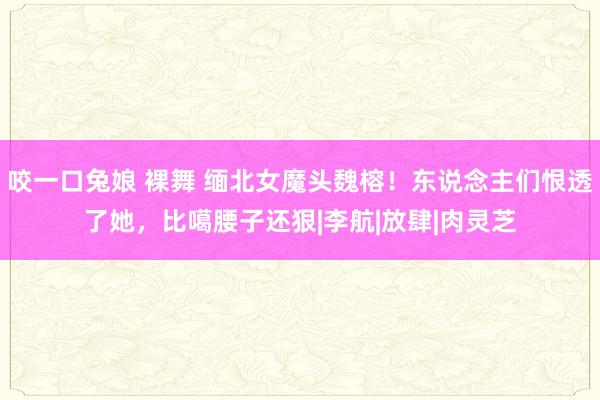
创作声明:本文为编造创作咬一口兔娘 裸舞,请勿与执行干系
魏榕,缅北的女魔头,在那片迢遥渊博的郊野中,险些是无东说念主不知的存在。她的名字在缅北流传,仿佛带着血腥和恐怖的气味。她统带着一帮罪无可赦的辖下,有益从事种种违警交易,从东说念主口贩卖到毒品私运,兼容并蓄。但是,她最令东说念主望风破胆的,不单是是这些缺陷,而是她那与生俱来的狠毒人性和不可阻遏的理想。
魏榕极其好色,尤其对那些刚骗进来的年青帅哥有着近乎放肆的执念。她可爱恣虐他们,享受着掌控一切的嗅觉,可爱看他们在她的按捺下怯生生发抖的口头。她的营地里频繁能听到令东说念主屁滚尿流的声息,伴跟着哀嚎和啼哭。被她选中的须眉无一避免。

新来的阿东是一个二十露面的年青东说念主,羸弱的脸上带着几许青涩和怯懦,但这恰是魏榕最可爱的类型。阿东不知说念我方是怎样被这帮东说念主骗到缅北来的。他的脑海中只剩下握住访佛的怯生生和无助。他被关在一个阴雨的房子里,房子里的空气迷漫着一股古老和血腥的滋味,让东说念主作呕。
一天夜里,阿东被两个壮汉拖到了魏榕的房间。魏榕坐在房间中央的躺椅上,驾驭是一个广大的木桶,桶里泡着一些血红色的液体,安闲着一股腥臭。魏榕盯着阿东,嘴角扬起一抹残忍的含笑。
“又一个簇新的小崽子。”她的声息低千里,带着一点玩味的淡漠。“来,过来让我望望。”
阿东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,魏榕的眼神就像一把芒刃,狠狠刺在他的心头。他挣扎着想要脱逃,却被壮汉死死按住,无法动掸。魏榕缓缓站起身,走到阿东眼前,用手指挑起他的下巴,将就他直视她的眼睛。
“你窄小吗?”魏榕舔了舔干裂的嘴唇,带着一点病态的简洁。“宽心,很快你就不会窄小了。”
说完,她忽然大笑起来,那笑声尖锐逆耳,仿佛能穿透东说念主的骨髓。阿东的眼泪夺眶而出,他嗅觉我正派一步步走向平川,而魏榕即是阿谁平川的愚弄。
魏榕千里迷于这种驾驭与被驾驭的游戏,她残忍而病态的理想让她衰弱其中,乐此不疲。阿东只是一条小鱼,而在她的网里,早已囚禁了巨额条鲜嫩的人命。他们在她手中挣扎、哀嚎,却始终逃不出她设下的樊笼。
魏榕对须眉的残暴并不啻步于浮浅的恣虐和折磨。她有一种病态的好奇——割下须眉的下体,泡在一种特制的溶液里,然后独自观赏,仿佛这是她自娱自乐的方式。她的营地中有一个机密房间,外东说念主难以窥察其究竟,凡是是她的挚友齐知说念,那是魏榕的“艺术室”。

房间中迷漫着一股令东说念主窒息的血腥味,空气湿冷,墙壁上挂满了种种各样的刀具,色播五月刀刃闪着冰寒的光泽。每一把刀齐有着它的故事咬一口兔娘 裸舞,而这些故事无一不被鲜血浸染。房间中央摆着一瞥群山万壑的玻璃罐子,罐子里泡着须眉的下体——这些被魏榕戏称为“标本”。她会将这些罐子次序排开,每天坐在它们眼前,带着一种令东说念主发指的洗澡脸色,细细端视,仿佛那是她创作的精品。
但是,关于魏榕来说,这些不外是她意思爱好中的一小部分。信得过让她沉迷的,是她称之为“肉灵芝”的东西——那是男性的睾丸。魏榕以为,这些看似柔嫩的器官荫藏着深重的能量。她的执念甚而让她笃信,食用这些“肉灵芝”好像延年益寿,甚而领有深重的力量。她每次活剥这些“肉灵芝”的经由,齐如消释个病态的庆典。
这天,魏榕又锁定了别称新主张——李航。李航是别称来自中国的小伙子,高大健壮,有着一张超逸的容颜。在魏榕的眼中,这恰是“肉灵芝”最佳的载体。她一经等不足要试吃这份“簇新”的滋味了。
在魏榕的营地,音书老是传得很快。魏榕对李航的意思引起了统共东说念主的疑望。莫得东说念主敢去辅导他,也莫得东说念主自得去惊扰魏榕的“狩猎”。一朝成为魏榕的主张,意味着你一经被判了死刑。魏榕会亲身制定狡计,怎样让“猎物”在苦处中逐渐崩溃,终末在灰心中献上她渴慕已久的“灵芝”。
她的辖下将李航带到“艺术室”时,他的双手被反绑在死后,嘴里塞着破布。李航脸色煞白,额头上盗汗直冒。他看到了墙上那些挂着的刀具,将强到了我方的运道,心中翻滚着无限的怯生生和灰心。
魏榕缓缓走进来,身上一稔一件玄色的皮衣,腰间别着一把泛着冷光的匕首。她的眼神如消释条毒蛇,冰冷而横暴。
“李航,”她轻声念着他的名字,仿佛在呼叫一个情东说念主,“今天你要给我献上一份大礼。”
李航的意见里充满了盛怒和怯生生,但他不行发声,只可发出模糊的抽咽。魏榕轻举妄动,她把手伸进一旁的桌子抽屉,拿出一瓶领略的液体。
“你知说念吗?‘肉灵芝’是一种神奇的东西,能让东说念主永葆芳华,元气心灵重生。”她的声息带着放肆的执念,“你很快就会阐明的。”
她的手缓缓划过他的胸膛,感受着他惧怕的肌肉。接着,她从腰间拔出匕首,用刀尖轻轻划过李航的皮肤,感受着他剧烈的惧怕。李航眼中充满了怯生生,但更多的是盛怒和仇恨。他不解白,为什么这么一个女东说念主会如斯残忍。
最新伦理片魏榕一步一时局麇集他,不息喃喃自语,仿佛在进行某种庆典前的祈祷。她用匕首在李航的大腿上划出了一起淡淡的伤口,鲜血缓缓渗出。然后,她运行准备她的“主菜”。
在她死后的桌子上,摆放着种种器具和药水。她选了一把最狠恶的手术刀,刀锋闪耀着冷光。魏榕将刀子举到目下,凝视了瞬息,似乎在感受它的狠恶进程。然后,她回身走到李航眼前。
“准备好了?”她柔声问说念,眼中闪耀着病态的简洁。
李航一经无法谈话,他的眼中尽是灰心。他知说念我方根蒂无法脱逃,她的辖下挥霍围在周围,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魏榕莫得给他太多念念考的时候,手术刀垂手而得地划开了皮肤。
李航发出一声肝胆俱裂的惨叫,但这更像是一种圆寂前的哀嚎。魏榕将手术刀缓缓刺入,看成轻巧但精确。她就像一位艺术家,在制作她心目中完好的作品。跟着刀子的深化,鲜血喷涌而出,染红了她的手和衣服。李航的体魄运行剧烈地抽搐,他的将强在剧痛中逐渐模糊。
魏榕将切下的“肉灵芝”捧在手心,细细端视,仿佛这是一件至极的艺术品。她将其放入早已准备好的溶液中,溶液中坐窝泛起一阵波纹。她的眼神变得狂热,仿佛看到了某种神奇的气候。
“你看,它多好意思。”她喃喃自语,完全无视了李航的存一火。
李航的体魄一经因为失血过多而运行抽搐,将强也渐渐模糊,但他的意见中依旧充满了仇恨。他用尽终末的力气,试图挣脱捆绑,却一经窝囊为力。
魏榕将溶液中的“肉灵芝”取出,防备翼翼地捧在手中。她缓缓将它凑到嘴边,仿佛在进行一场皎白的庆典。她伸开嘴,轻轻咬了一口。
那刹那间,她的眼神里尽是洗澡,仿佛这一刻她得到了长生。
营地外,暮色渐千里,风声中混合着一点冰冷的寒意。而在这座血腥的“艺术室”中,魏榕的病态艺术还远远莫得为止……
魏榕的“艺术室”依旧保合手着那股强烈的血腥味。空气中充斥着怯生生与灰心的气味,而魏榕仍然千里浸在她那无限的薄情理想中。她一经活剥了三十多位须眉的“肉灵芝”,每一次,她齐乐此不疲地享受这种病态的快感。但是,她却莫得预感到,这一次,她的残忍会为她招来打消。
那天,魏榕挑选的“猎物”是一个被称为“阿明”的须眉。他是营地里少数几个还保留着不满和抵牾意志的东说念主之一。阿明身段肥大,肌肉阐明,明显是个有搏斗力的男东说念主,但他在魏榕眼里不外是下一个“作品”的原材料。魏榕自信满满,从未想过一个俘虏能对她变成任何威迫。她的辖下齐是狼心狗肺的凶徒,岂论谁敢挣扎,齐唯有绝路一条。

阿明被带到“艺术室”时,他的眼中透出一种与其他受害者不同的光泽,那是一种老羞变怒的决绝。他的手被反绑,嘴里塞满破布,步骤踉跄地被推入房间。但他莫得流披露怯生生,反而狠狠盯着魏榕,眼神中闪耀着盛怒与不服。
魏榕一稔她惯常的玄色皮衣咬一口兔娘 裸舞,手里拿着一把狠恶的手术刀。她舔了舔嘴唇,仿佛一经在品味接下来的血腥工夫。她走到阿明眼前,轻声说说念:“你知说念吗,你是我见过最意旨的猎物。你看起来很雄厚,也许你的‘肉灵芝’会更有韧性。”
